2025年3月26日,梅賽德斯-奔馳自動駕駛業務高管喬治·馬辛在柏林行業會議上發出警告,稱歐洲車企因過度依賴中美技術而陷入風險,并呼吁歐洲加強自主創新。這番言論看似憂患意識濃厚,卻暴露了奔馳在技術路線上的矛盾性,既無法擺脫對中國技術的依賴,又未能構建真正的核心競爭力。反觀奧迪、大眾、寶馬等歐洲車企,其與中國企業的深度合作正成為轉型破局的關鍵路徑。
合作是技術迭代的必然選擇
馬辛的“依賴論”直指歐洲在AI芯片、云計算等領域的短板,但這一現象并非歐洲獨有,而是全球技術分工的必然結果。以大眾為例,其因軟件研發受挫轉而與地平線合作,推動ID.家族智駕系統落地中國市場;奧迪則通過引入Momenta的ADAS技術,提升本土化競爭力。寶馬更是在沈陽建立全球最大研發中心,聯合中國團隊開發新一代智能座艙。

這種合作本質上是技術互補:歐洲車企提供機械工程積淀,中國企業貢獻算法與算力優勢。例如,大眾與地平線聯合開發的L2+級智駕系統,算力較上一代提升4倍,成本卻降低30%。正如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曾經指出的,閉門造車的時代早已結束,合作是保持競爭力的唯一路徑。
中國車企的“自主”進階,是合作共贏的最好證明
中國車企的崛起,恰恰證明了所謂的“依賴”與“自主”并非對立。比亞迪通過自研刀片電池與e平臺3.0,打破日韓對動力電池的壟斷;蔚來依托全棧自研的NAD系統,實現高速領航功能覆蓋全國95%路段。更關鍵的是,中國車企已從市場換技術轉向技術定義市場,華為ADS 3.0、地平線征程系列芯片等技術輸出給傳統豪華車企,反向賦能其智能化轉型。

這種角色轉換的背后,是中國每年超過1.5萬億元的研發投入(占GDP 2.4%)與全球最大智能汽車應用場景的支撐。2024年,中國自動駕駛專利數量占全球43%,遠超美國的29%。正如波士頓咨詢報告指出所言,中國正從技術消費者轉變為技術生產者,全球汽車產業鏈權力結構已發生根本性偏移,這些無不體現了中國自主車企從追隨者變成引領者。
奔馳與其警惕行業,不如多在意自己
馬辛的焦慮,本質是奔馳技術路線失敗的投射。作為最早布局電動化的豪華品牌,奔馳卻陷入老生常談的泥潭。新能源浪潮之下,2024年奔馳在華新能源滲透率僅3%,遠低于行業40%的平均水平。MB.OS系統多次推遲發布,高階智駕僅限旗艦車型,與華為、小鵬的全棧能力差距顯著,雖投資Momenta,但核心算法仍依賴外包,未能形成技術閉環。

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戰略搖擺,一邊抱怨依賴中美技術,一邊為降低成本縮減研發投入,資料顯示,2024年研發費用同比下降15%,一邊高喊本土化,卻在中國市場裁員15%,削弱技術響應能力。這種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態,只能說作為百年大廠實屬讓人啼笑皆非。
汽車網評:合作不是原罪,封閉才是危機,馬辛口中的依賴,實則是奔馳對自身無能的辯解。即便是同為歐洲大陸上的車企,奧迪憑借PPE平臺與智己聯合開發純電車型、大眾和小鵬合作,奔馳卻始終在自怨自艾。歷史早已證明,汽車產業的進步從來依靠開放與合作。
在智能電動化浪潮下,拒絕合作者終將被時代拋棄,正如《經濟學人》所言,未來的贏家不屬于最封閉的企業,而屬于最懂協同創新的玩家。奔馳若繼續沉溺于依賴焦慮,下一個被淘汰的會是誰,不言而喻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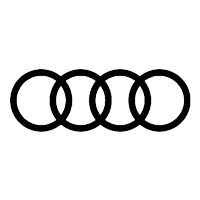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010602000157號
粵公網安備 44010602000157號
